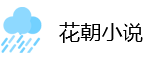作为专业人士,杨靖恩从走进奶牛场的那一瞬间起,便捕捉到有价值的技术信息。他在场内转了一圈,便对奶牛场的工作,有了初步的认识。
五十头奶牛,分别定位在两排定位栏上,头朝外,屁股朝内。头朝外方便奶牛呼吸新鲜空气和采食;屁股朝内,便于奶牛排泄粪尿入地漏;也便于挤奶操作。挤出来的牛奶,通过机械管道即时输送到致冷房贮存。
杨靖恩从桥本夫人了解到,酪农协会的牛奶车定时到奶牛场收奶。奶牛吃的配合饲料,由饲料公司提供;干草和青贮玉米,酪农家自行备料。奶牛排放的粪尿,通过地漏聚集到地下沟槽;除臭方法是,通过往地沟拨撒除臭剂来解决。
奶牛场的管理,基本由桥本夫人一个人承担,早晚各挤奶一次。
整个奶牛场,结构紧凑,环境洁净,虽然牛舍和家居的距离不到十几米,牛舍和外围公路只是布帘之隔,但却闻不到浓重的臭味。
夜幕降临时,杨靖恩和桥本夫人共同完成奶牛场的工作。此时到肉牛场工作的桥本俊也正好同步完工回到家里。
桥本俊回到家的第一个动作,就是走进浴室洗澡。
杨靖恩坐在餐桌旁,此时才有机会仔细打量眼前的景物。厨房不大,约有八、九平方米。设有三个门,一个通往院子,一个通往客厅,一个通往浴室。
桥本夫人早已换上休闲服,正专心细致准备丈夫的晚餐。杨靖恩从侧面打量桥本夫人,换下臃肿工作服的她,原来也十分耐看,粉嫩的肤色,挺拔的胸脯,微微翘起的臀部,彰显出哺乳期少妇的成熟美。
当桥本夫人转过正面,杨靖恩暗中欣赏她的脸,稀疏的刘海,遮盖不住弯弯的柳叶眉,两泓勾魂的杏仁眼下面,长着挺直秀气的鼻梁,两颊绯红的瓜子脸,配上似笑非笑的樱桃小嘴,让人心生怜惜,百看不厌。
她为丈夫准备了一个备份的生菜,还有一份烤鱼。生菜的制作很简单,把冲洗干净的整叶生菜放进钵子,撒上一些香油和酱油,就算大功告成。
桥本俊从浴室出来,像大臣宣布皇上上朝一样,大声嚷嚷:“杨桑,噢咐洛!(洗澡),”然后就旁若无人地享用晚餐。
杨靖恩“嗨”了一声,然后奔上二楼,拿起待换衣物就往浴室跑。直觉告诉他,桥本俊已经把他排在这个家庭的老二。
按习惯,F国人洗澡也要论资排辈,一般,家长排第一,父亲排第二,儿子排第三,母亲排第四,女儿排第五,媳妇排最后。
照此推断,杨靖**到这个家的第一天,就被这家人当儿子看待了,因为桥本俊的父亲不在这个家庭生活,一个人独居在养老院。杨靖恩作为排第三的儿子辈,一跃上到第二位了。
进到浴室,那缸看似脏兮兮的浴水,立即映入杨靖恩的眼帘。那缸浴水,飘浮着桥本俊的体脂,水气袅袅;之前,早听闻F国人有这种坏习惯,即全家人轮流泡一缸浴水的坏习惯,直到最后洗澡的人泡完,才排掉那缸脏水。今儿个亲眼目睹了,验证了那种传说,杨靖恩不免产生一阵一阵的恶心。他站在远离那缸浴水的角落,打开花洒,任凭花洒从头淋到脚,他刻意用这种方式,从心里、从行动上与那缸浴水划清界线。
等杨靖恩淋浴结束走出浴室,桥本俊早已不知去向,无影无踪。
桥本夫人照例为杨靖恩准备了简单的晚餐:一份烤鱼、两个荷包蛋和一钵生菜。她催促杨靖恩快快用餐。
细心的杨靖恩发现,自已的菜谱多了两个荷包蛋,便问桥本夫人道:“噢托桑(父亲)不吃鸡蛋吗?”
桥本夫人:“不是,是来不及为他做!”
杨靖恩:“噢托桑(父亲)要赶去哪儿那么急?”
桥本夫人:“不知道,从来不敢问,他爱去哪就去哪。如果他洗澡出来,不得马上吃,他会不高兴的。”
杨靖恩:“原来如此!”
“噢咔桑(妈),您不是也没吃吗?我们一起吃吧!您抱小孩不方便,我为您盛饭。”杨靖恩边说边看着桥本夫人。
“不不,我们家是噢托桑(老爸)先吃,其他人后面吃。”她抱着小女孩一动不动。
“为什么?”杨靖恩问。
“规矩和礼节。”桥本夫人答。
“我的家乡,远古时候也这样,那是孔孟时代了,现在已经不同。现在的社会体现男女平等。就我而言,撇下家人自己吃,无论如何是吃不下的。”杨靖恩面对桥本夫人,边用F国语言吃力地表达,边用手语比划来辅助情感。
桥本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杨靖恩:“您说的,我能听得懂。不难想象,做你们国人的太太一定很幸福!”
“不如我做个中国料理让您尝一尝吧?”杨靖恩从桥本夫人的眼光,读到一种异样的电波,他不得不转移话题。
“杨桑会炒菜?需要什么材料?”桥本夫人很惊讶的样子。
杨靖恩:“会,会炒很多种,我做过酒店的经理呢!简单炒个青菜给您尝尝吧。材料很简单,有油盐和蒜米即可。”
“那就有劳杨桑咯!”桥本夫人的柔情细语,好像要把杨靖恩融化似的。
杨靖恩故意避开桥本夫人的锋芒,专心细致地炒菜。桥本夫人抱着小孩,离杨靖恩很近,杨靖恩简直可以闻到小孩的奶味和女人的体香。
一会儿功夫,一碟香喷喷的蒜茸炒青菜,便被杨靖恩捧上身后的餐桌。
桥本夫人执意不吃饭,她自己拿来小碗和一双筷子,品尝起杨靖恩炒的青菜来。边吃边赞不绝口:“好吃,非常好吃!”
这是杨靖恩在异国他乡第一次炒菜,桥本夫人是第一位陪他用餐的F国女人。
也就是这碟青菜,成为这两个不同国籍、不同性别、不同文化层次、不同家庭背景的陌生人相互交流的起始媒介。
桥本夫人信手拿来一支笔和一本软皮抄,遇到杨靖恩听不懂的内容,就用汉字来表达。
杨靖恩:“见到奶奶,没见到爷爷,爷爷去哪儿?”
桥本夫人:“爷爷独自住在国家安置房小区,很少回这儿。爷爷奶奶都七十二岁了。”
杨靖恩:“两个闺女叫什么名字?”
桥本夫人:“大的叫做桥本瞳,十三岁;这个小不点叫桥本真美,七月龄。”
杨靖恩:“冒昧问一下,两姐妹年纪相差那么大,是什么原因?”
桥本夫人:“我们曾经有一个儿子,四岁时被狼狗咬伤至死...去年才想起,再要一个小孩。”桥本夫人的脸上掠过一抹浓重的哀伤。
杨靖恩:“浴室里有一个精致的口杯,上面写着‘桥本政世’,那名字就是令郎吗?”
桥本夫人:“是,那是他留下的唯一遗物。杨桑真细心。”
杨靖恩:“对不起,我令您想起伤心的往事了。”
桥本夫人:“没什么,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。杨桑,您到这以后就开始忙碌,还没给家人报平安呢!打个电话吧。”
杨靖恩:“算了,明天再写信。我们有规定,不可以乱用老板的东西。”
桥本夫人:“规定是死的,人是活的,再说不是有我在这里吗?您就放心打吧。”
杨靖恩:“恭敬不如从命,那我就打咯。”
杨靖恩用最快的速度给家里打了越洋电话。桥本夫人在旁边,笑眯眯地看着。
杨靖恩掛断电话,桥本夫人问:“杨桑,您的太太一定很漂亮很贤慧是吧,听话筒里传出来的声音,那么悦耳,那么柔美,小孩几岁?男孩还是女孩?”不等杨靖恩坐回原位,桥本夫人又聊开了。
杨靖恩有些腼腆和手足无措,弱弱说道:“家内(妻子)容貌智慧一般般,小男孩六岁,正读学前班。”
桥本夫人:“杨桑那么优秀,小孩一定很聪明吧?”
杨靖恩:“夫人过奖了,我们都是凡人。”
桥本夫人:“杨桑读大学的时候就选修F国语言吗?”
杨靖恩:“没有,赴F国研修前短训四十五天。”
桥本夫人:“那么短的时间,就学得那么好呀?”
杨靖恩:“见丑了,我现在的F国语言还说得不流利。其实我们研修生也是被逼出来的,不下一番功夫,现在就寸步难行了。”
桥本夫人:“说的也是。”
杨靖恩:“哎,要是也给您学四十五天汉语,敢去中国吗?”杨靖恩话一出口,就感觉有点藐视对方意味,但来不及改口了。好在桥本夫人不介意,她还是顺着杨靖恩的思路说下去:“哪敢哟,别说四十五天,就是四年半也不敢保证啊。”
杨靖恩:“夫人,您太谦虚了,其实您非常聪明。”
桥本夫人:“是吗?我第一次被别人夸奖,而且还是一位外国的帅哥!”
杨靖恩:“真的吗?夫人天生丽质,又那么能说会道,不会没有人欣赏吧?”
桥本夫人:“杨桑,您说得我脸红了!”
杨靖恩:“脸红更显出您的妩媚,我说的是真话。”
桥本夫人:“中国男人很温存,不像F国男人小肚鸡肠!”
杨靖恩:“不会吧?”
桥本夫人:“是的,F国男人脾气还很大!”
杨靖恩:“不好意思,时间不早了,我得上楼温习一会儿功课了。”
桥本夫人:“好的,来日方长,改日再聊。”桥本夫人意犹未尽。
杨靖恩:“忘记问了,早上几点开始工作?”杨靖恩转回身子,面对桥本夫人问。
桥本夫人:“一般五点半,您初来乍到,对环境不适应,不必起得那么早。”桥本夫人貌似很体贴的样子。
杨靖恩:“明白了,夫人晚安!”
说晚安,其实是树欲静而风不止,杨靖恩上到二楼卧房,突然感觉六神无主,那些已经发生和尚未发生的事情,组成无数个幻灯片,争先恐后在杨靖恩大脑中放映,令他坐卧不安。他手里捧着书,却来回看的都是同一行的字。他索性丢开书本,躺在榻榻米上,但辗转反侧睡不着。他想家,想妻子,想儿子;想过去的一切,想今天的一切:想早上还在上海,下午就到F国,晚上就睡在F国的酪农家里;想糊里糊涂成为这个“女儿国”的“皇太子”,一个人睡在当年老板结婚的洞房里;想一齐来的另外二十位弟兄,现在是不是也失眠...